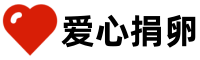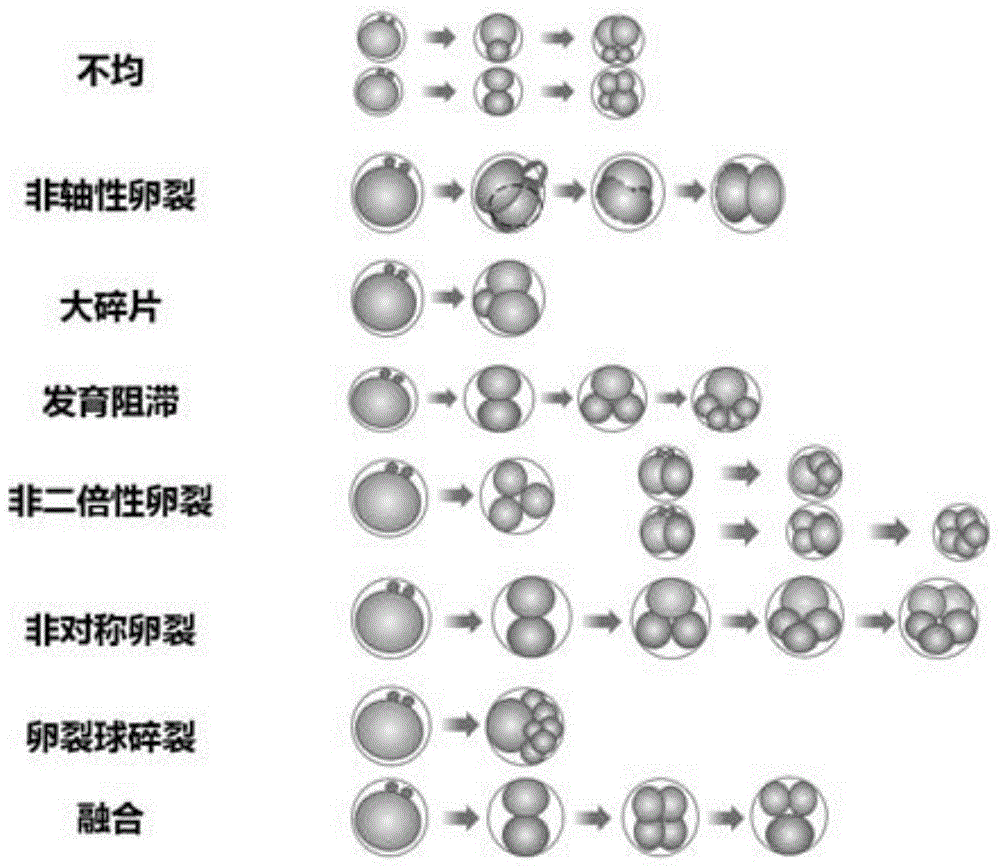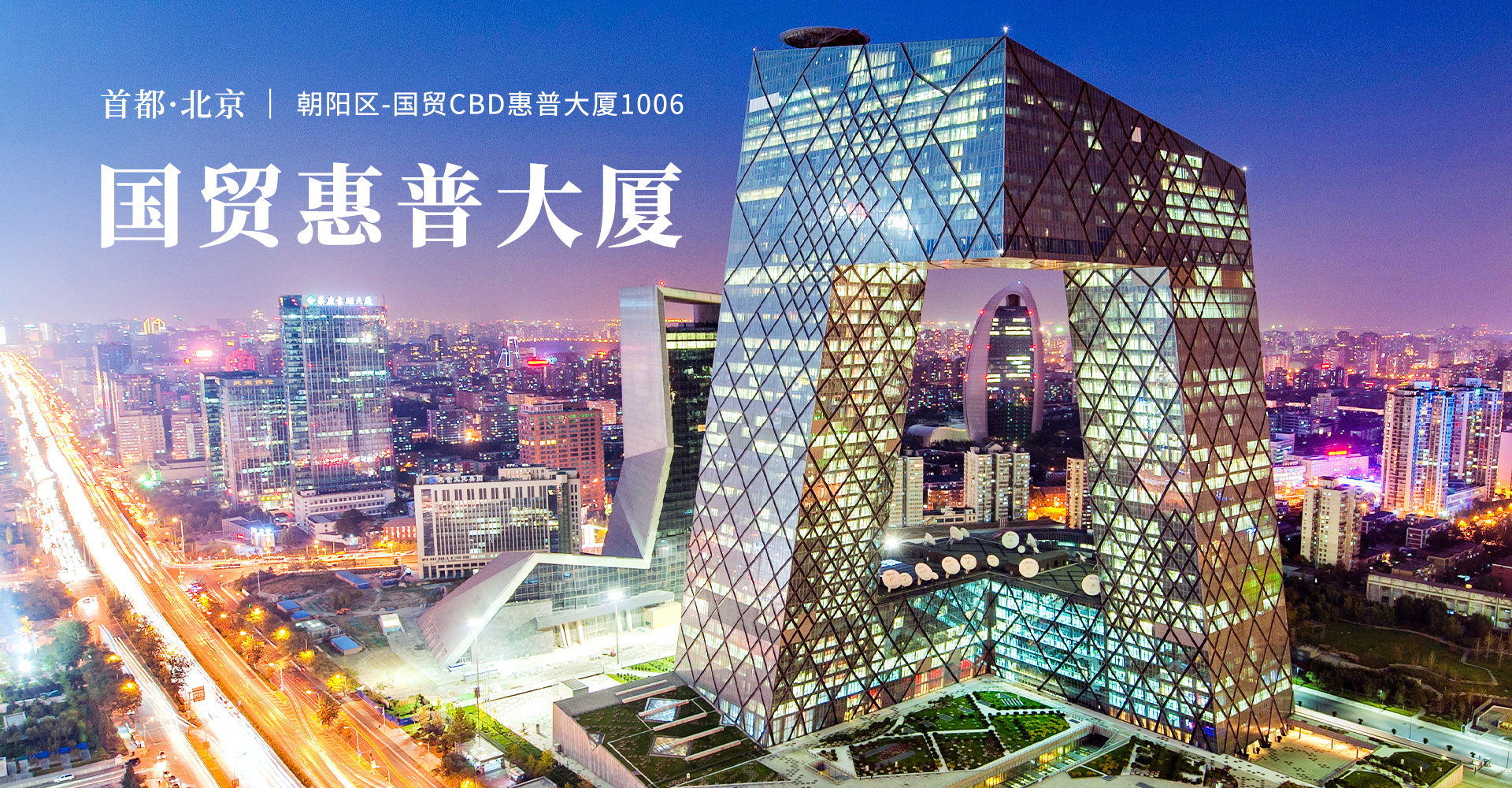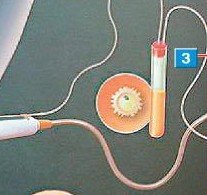
对于无法自然受孕的人来说,捐卵助孕提供了一种创新的解决方案。捐卵助孕涉及使用捐赠者的卵子进行体外受精(IVF),然后将受精卵植入准母亲的子宫内。这种技术使那些由于卵巢功能障碍、染色体异常或其他因素导致不孕的人能够生育子女。

添加微信好友, 获取更多信息
复制微信号
捐卵助孕的过程
捐卵助孕的过程包括以下步骤:
- 初次咨询:与生育专家会面,讨论捐卵助孕的选项并评估您的合格性。
- 卵子捐赠者匹配:从捐卵者数据库中匹配一位与您生理特征相似的卵子捐赠者。
- 卵子捐赠者准备:捐赠者接受药物治疗以刺激卵巢产生多个卵子。
- 取卵:通过手术从捐赠者卵巢中取出卵子。
- 体外受精(IVF):将捐赠者的卵子与您的伴侣的精子在实验室中受精。
- 胚胎发育:受精卵在实验室中培养并形成胚胎。
- 胚胎移植:将一个或多个胚胎植入准母亲的子宫内。
- 妊娠监测:准母亲接受定期检查以监测妊娠进展。

捐卵助孕的优点
- 提高受孕率:捐赠者的卵子通常年轻且健康,这可以极大地提高受孕的可能性。
- 降低遗传风险:捐赠者的卵子经过筛选,没有已知的遗传疾病,这可以降低孩子患遗传病的风险。
- 满足卵巢功能障碍患者的需求:卵巢功能障碍导致不孕症的女性可以通过捐卵助孕实现生育梦想。
- 允许已婚同性伴侣生育:女性同性伴侣可以通过捐卵助孕生育生物学上相关的孩子。
捐卵助孕的挑战
- 高昂的费用:捐卵助孕是一项昂贵的程序,费用可能在数千美元到数万美元之间。
- 情感挑战:对于一些准父母来说,使用捐赠者的卵子可能会产生复杂的情感,例如对孩子的归属感问题。
- 捐赠者短缺:卵子捐赠者短缺可能是影响捐卵助孕可获得性的一个挑战。
捐卵助孕的法律和伦理问题
捐卵助孕涉及复杂的法律和伦理问题。这些问题包括:
- 亲子关系:亲子关系的法律地位,特别是如果捐赠者或准父母决定在未来联系孩子的情况下。
- 捐赠者权利:捐赠者的权利,包括在捐赠后解除匿名权或获得孩子健康信息的权利。
- 伦理考虑:捐卵助孕对捐赠者和其他参与者(如代孕母亲)的伦理影响。
结论
捐卵助孕是一种创新的解决方案,可以为许多无法自然受孕的人创造生育的机会。虽然它提供了一些优点,例如提高受孕率和降低遗传风险,但也有一些挑战,例如高昂的费用和情感挑战。重要的是要仔细权衡捐卵助孕的利弊,并与生育专家讨论,以确定它是否适合您的情况。
助产士接生的方法
妇产科医师和助产士通力合作让生产回归自然在科技与人文之间,人类永远有难以摆平的平衡问题,进步神速的科技,即使能够巧夺天工,终究不能「人定胜天」,否则大自然的反扑,绝非人类所能抵挡。 生殖医学带来捐精、捐卵、借腹生子、复制胚胎、复制人等种种令人既喜且忧的新科技新问题,未来将成为二十一世纪人类争议的主题之一。 然而,先不谈这些新科技,光是所有生物与生俱来的本能,传宗接代,人类就已经面临了科技带来的诸多问题,以致必须省思是否应该复古,应该回归自然,才符合人类最大的利益。 ◎剖腹生产率为何偏高 引发这种思考的主因之一是,台湾地区的剖腹生产率在过去二十年之中,增加了一倍以上,记得一九八○年代初期,当我开始成为妇产科医生时,台湾的剖腹生产率约为15%,九○年代变成三分之一以上的生产是剖腹产,也成为公卫学界及妇女团体抨击的主要议题之一。 剖腹产率节节上升的原因很多,主要的是: (一)生率数下降,人们普遍期待生一个活一个,而不像五○年代可以生一打,夭折两、三个是常态。 母子均安的强烈期待,对妇产科医生无疑是一大压力。 (二)医疗纠纷日益增多,产科已经成为众所周知的危险科别,剖腹产无疑的可以比等候自然分娩更有把握使胎儿减短处於「黑箱作业」的状态中。 (三)胎儿监视器的发明,固然挽救了无数的受窘迫中的胎儿,但也由於过度诊断而造成一些不必要的剖腹产。 (四)社会的功利主义,使得部分医师受到影响,以剖腹产来提高收入;不过在健保制度拉近自然产与剖腹产的医师费给付之后,这个因素已有部分减少。 (五)前胎剖腹产未能尝试自然产,使得大量头胎剖腹产的孕妇,几乎没什麼机会选择第二胎以后自然分娩,这也占了剖腹产率难以下降的一大原因,不过除非生产空间改善(有些医院至今仍未在产房中设立剖腹产用之开刀房,如此则万一前胎剖腹产之子宫破裂,还要转送到一般开刀房,这使得妇产科医生敢冒母子均危的风险去做自然分挽的尝试。 ),以及医疗纠纷的风险下降,否则这点仍不易改善。 (六)产前诊断的进步,使得部分先天性疾病得以事先看出来,而以剖腹产提高新生儿的存活率。 (七)部分民众迷信择日看时,以为高龄产妇无法自然分娩(现在的高龄产妇比二十年前所占的比率多了一倍以上),以为唯有剖腹产才能保持局部的身材,以为只有剖腹产才可减少产痛等等……不正确的观念也使得台湾地区的剖腹产率居高不下。 当我们看到日本和许多欧洲先进国家的剖腹产率,都一直维持在10%以下,甚至5%,能不汗颜?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台湾的情形孰令致之?卫生行政当局、医师、产妇及家属,乃至於整个社会,其实都有责任。 马偕医院针对过去三十年来剖腹产率变动趋势的研究显示,剖腹产率上升到15%时,周产期胎儿罹病率及死亡率,都有明显的下降,到20%以上时,则周产期胎儿的状况已不会再更好。 而目前各大中小医院的剖腹产率,大部分都在三成以上,低於25%的已属凤毛麟角,显然我们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努力。 ◎生产医疗化教我们不得不深思生产方式是否妥当的另一大原因是,目前在医院生产总令人有不自然且缺乏人性的感觉。 一方面,生产本身是一种生理的,而非病理的过程,然而为数甚多的非高危险群产妇,却被待之如病人;另一方面,即使是病理性的非正常产程产妇,他们所受到的照顾,也令人有人性化不足的感受。 比方说很多医院不分青红皂白,所有的产妇一入院待产,一律禁食、打上点滴、灌肠、腹部装上胎儿监视器……,一连串的动作,虽非酷刑,但却使得产妇有被剥夺行动自由的感受,同时也有人人都准备随时可能剖腹生产之感。 这些处置当然有其医学上的作用,但是否必须对每一位产妇都做?是否为了方便医院或医疗人员更具於方便产妇?在在值得我们深思。 在西方,即使是小小的一个剃除外阴的毛发(不包括耻丘部的毛),对产妇是否真的利多於弊都引起了重视,值得我们参考。 至於准爸爸进产房(接生室)陪产,LDR(乐得儿,即从待产、生产到产后恢复都在同一个房间)、母婴同室、产台餵奶…等人性化的措施,西方国家已推展了十多年,台湾则至今绝大部分的医院都没有动作,这当然也牵涉到多方面,不过只要有心,应该也不太难达成。 其实对产妇而言,缺乏人性化关怀的感觉,可能从产检就开始了,由於大部分的妇产科医师平均每一小时看诊一、二十个以上的患者,如同一般的病人一样,孕妇也没有分配到多少时间,这当然也跟目前的健保制度下,诊察费偏低有关,不过如果有一些配套措施,例如由对生产过程十分内行的助产士从旁协助解说,去除孕妇的焦虑和疑惑,则状况还是可以改善的。 ◎居家生产是否可行当在医院生产变成一种令人感觉不自然、不自在、不自主的事情时,真正应验了「物极必反」的道理,有些人开始追求复古,希望在家中生产,一如四、五十年前的台湾一样,这样的心态是可以理解的。 问题是当年的周产期罹病率和死亡率,以及孕产妇的罹病率和死亡率都很高,这些方面能够进步到今天的水准,主要有赖於抗生素的研发,胎儿监视器和超音波的发明与应用,而这些唯有在医院诊所生产才使得上力。 理论上,如果能够完全区分出高危险群和低危险群产妇,则我们可以将低危险群交给助产士,让产妇在家中分娩。 问题是以目前科技之发达,大约也只有百分之七十的生产「意外」状况,可以事先预测出来,仍有三成左右的状况,至今还是在产程中才能看出来。 即使把低危险群产妇交给助产士处理,如在家中分娩,发生意外状况,如何来得及转送到医院?即使在医院中,都还有担心产房中没有剖腹产房间和设备,转到一般开刀房,来不及抢救的状况,更何况是在家中,还必需叫救护车。 如以台北市的交通状况而言,一般病患「死於交通阻塞」的情形屡见不鲜,如将产妇也置於同一情况,岂不是原本生理的变成病理(本身)加病理(外在),亦即雪上加霜?以产科急症胎盘早期剥离而言,固然有些孕妇原本即属於高危险群,但是仍有许多病例,事后检讨起来,完全找不出危险因子,却在产程中突然出现胎盘早期剥离,有些就在几分钟之内,胎儿迅即死亡。 再以妇产科医师之梦魇羊水栓塞为例,产妇往往在产中或产后,突然发生呼吸困难,步向死亡之路,在医院中抢救都很困难,更何况是在家中!俗语说:「生得过麻油香,生不过四块板」(台语)。 对多数产妇而言,生产是一种生理现象,然而对某些产妇而言,犹如鬼门关前走一回,更不幸的则是根本走不过去,且事先又没有徵兆。 针对在医院生产和居家生产的比较研究,其研究样本必须相当庞大,也许必须至少二十万个以上才行,因为目前在医院生产的母体死亡率极低(十万分之一、二),周产期状况也相当好,如果没有超大规模的研究样本,恐怕看不出中间的差别。 当然,如果针对产妇及家属的感受来看,居家生产较具人性化,应该是无庸置疑的。 另外,以目前台湾地区的医疗纠纷已经是四、五十年前的千百倍数量(官方登记的只是冰山一角)来看,居家生产由於对母体及新生儿的急救比在医院有更大的限制,如果鼓吹起来,恐怕会有更多的纠纷。 总而言之,居家由助产士接生,顺利的话可能满意度会比在医院生产高,但不顺利的话,所产生的不良后果恐怕是难以弥补的。 目前妇产科医学界普遍认为,这是开倒车的做法。 ◎改善之道目前国内领有助产士执照的五万人之中,只有不到一千人登记执业中,助产所仅剩二十家,的确是人力资源的浪费;然而如果为了追求更人性化的生产环境,为了降低剖腹产率,而鼓吹居家助产士接生,则又衍生出新的问题,尤其是较高的生产风险。 记得一九八○年代末,我在南加州大学医学中心妇女医院时,每月该院有一千八百位产妇,可能是全球规模属一属二的产科中心,院内有两个产房,一个用来训练住院医师,一个用来训练助产士,产妇入院时由一位总住院医师在急诊处就根据各种资料,归类为低危险群的,亦即足月、没有过期、不太大、不太小、胎位正常、没有破水、没有母体高血压、糖尿病、发烧、吸毒……即送入助产士负责接生的产房,如有任何状况的则送入医师负责接生的产房。 在助产士接生的产房中,有总住院医师作后盾,一旦产程异常、胎心音异常……则由医师接手处理。 由於那是一所主要目的在训练医师和助产士的教学医院,也许人性化的生产环境和制度,未必尽如人意,不过记忆中助产士接生的产妇满意度的相当不错。 我个人心目中的改善之道,既不是复古的助产士到府服务,也不是助产士在助产所接生,而是南加大模式的修正。 我的看法是,将闲置的助产人力找回来,进入医院诊所的产房,让她们作第一线的处理,可以一对一或一对二地全程陪伴产妇,如果产妇同意,低危险群的也可以由助产士接生,有状况的则随时由妇产科医院接手,这样大概不但会有较令人满意的生产照顾,也会降低一部份剖腹产率。 这种情形,有一点类似其他医学专科中的技术员或专科护理师,例如麻醉科中的麻醉护士,事实上她们在麻醉医师的指导下,执行了台湾地区绝大部分的麻醉工作。 在妇产科住院医院一年比一年少的情况下,如能把助产士重新带回医疗体系中,给他们一定的执业空间(事实上从产前检查开始,助产士就可以和医生一同看诊),生产照顾和医疗品质应会有所提升。 一个比较伤感情的问题是,乃有医疗纠纷,医师和助产士之间的责任如何划分?因为助产士既已独立接生(而非只是医生接生时的助手),则不可能完全不负担风险,这一点必须先拟定出一个可行的方法来。 另外,既有专业风险,也应该有专业收入,健保局不妨深入研究规划,表面上可能多付一笔钱,但如果因而减少一些剖腹产,如果因而提高生产品质,则也许反而是省钱呢!不论是在目前制度下的医院生产,亦或是另外设立更没有医院感觉的生产中心(Birth Center)对於生产过於医疗化,缺少人性化的问题,事实上只要医院主政者、医师以及健保局配合,情况绝对是可以改善的。 辅英技术学院设立助产学系和台北护理学院设立护理助产研究所,显然将在二十一世纪提升台湾助产水准的目标上沟出了一大步,如果妇产科医师和助产士能通力合作,相信未来我们可以期待更符合自然与人性的愉快生产经验,这才是全民之福。
试管婴儿与和第三方辅助生殖有什么区别
在我国经常把 “体外受精 -胚胎移植 ”(IVF -ET )叫 “试管婴儿 ”,从1978年第一例试管婴儿诞生至今发展了40年,发展经历了第一代试管婴儿、第二代试管婴儿、第三代试管婴儿。 第一代试管婴儿是精子和卵子在体外自然受精后将胚胎植入子宫后着床、发育最后分娩胎儿。 主要解决女性输卵管梗阻、宫颈因素和免疫因素导致的不孕。 第二代试管婴儿是利用显微操作技术将活力旺盛的精子注射到卵细胞内,使其完成受精。 主要解决男性不育、常规体外受精失败导致的不孕。 第三代试管婴儿是从卵母细胞胞浆内单精子注射受精得到的胚胎中取1至几个细胞 ,检测其染色体或致病基因 位点 ,将染色体正常和不携带遗传病的胚胎移植入子宫 , 从而保证妊娠胚胎的正 常,防止遗传病患儿的出生。 主要解决易产生染色体异常胚胎或有遗传疾病患者的生育问题。 而第三方辅助生殖除了上面提到的试管婴儿技术还包括捐卵、捐精、代理妊娠等内容。
允许 30 岁以上未婚女性生育一胎,你赞成吗?
对于这个问题,我觉得是赞成的,具体是为什么我下面会详细的聊的。
首先现在我国生育率年龄的下跌,在最近这一两年已经是跌破了“警戒线”了,据网上有新闻报道说,就在去年生育的人口比死亡的人口才多了不到50万,这几乎是接近了生育的零增长。 特别是对于我们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来说,这点人口增长微不足道。 为此国家也在不断地颁布各项政策,包括鼓励大家生三胎呀,多给女性一些生育的假期等补贴,但从大家的反应来看,这些补贴和国家的鼓励似乎没有什么效果。 年轻人们还是越来越晚结婚,并且不太愿意生孩子,已经生了一胎的,也不太想再生第2胎,而原本已经背负了很大压力的半年后,有了两个孩子如果再生育一个,压力也会更大。 所以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也许30岁以上未婚的女性生育一个孩子,我觉得是可以的。 这既能弥补国家的一部分生育率的问题,也能让那些年龄稍微大一点,但是又想要孩子,而且又不想结婚的女性满足他们的生存需求。
另外在现代的这个婚姻制度确实不仅仅是爱情这么简单,有更多的成本,两个家庭的结合日常生活的矛盾,感情的维系,包括生活当中的柴米油盐,再加上现在的年轻人越来越独立,思想也越来越开放,更加的自我,也更加不愿意被家庭所束缚,所以这样独立的个体,他很难是捆绑在一段婚姻当中。 特别是女性。 有了自己的经济能力,话语权,他在婚姻当中的选择空间就更大,甚至都可以不选择婚姻,原本每个人都带着自己原生家庭,影响在自我成长,但这中间可能遇到很多的不幸,包括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啊这些不幸的婚姻,会导致这些女性对婚姻丧失信心。 另外有一些女性为了不留遗憾又想要生孩子,那这样的一个需求也是合情合理的。
还有根据个人的经验来看,确实现在越来越多女性对于婚姻她没有像以前那么强烈的冲动。 越来越多人不会认为到了什么样的年龄做什么样的事,大家也越来越习惯一个人今天还看到一个数据说,疫情期间,我们有1亿多的人是过着独居生活的,可见这样的一个人群的数量是多么的庞大,这些人能自给自足,他们也不需要另一半也不需要有太多的束缚,但是考虑到养老啊或者是一些生活陪伴的问题,又想要有一个孩子。 所以这个时候出台这样的一个政策也是值得商榷的。